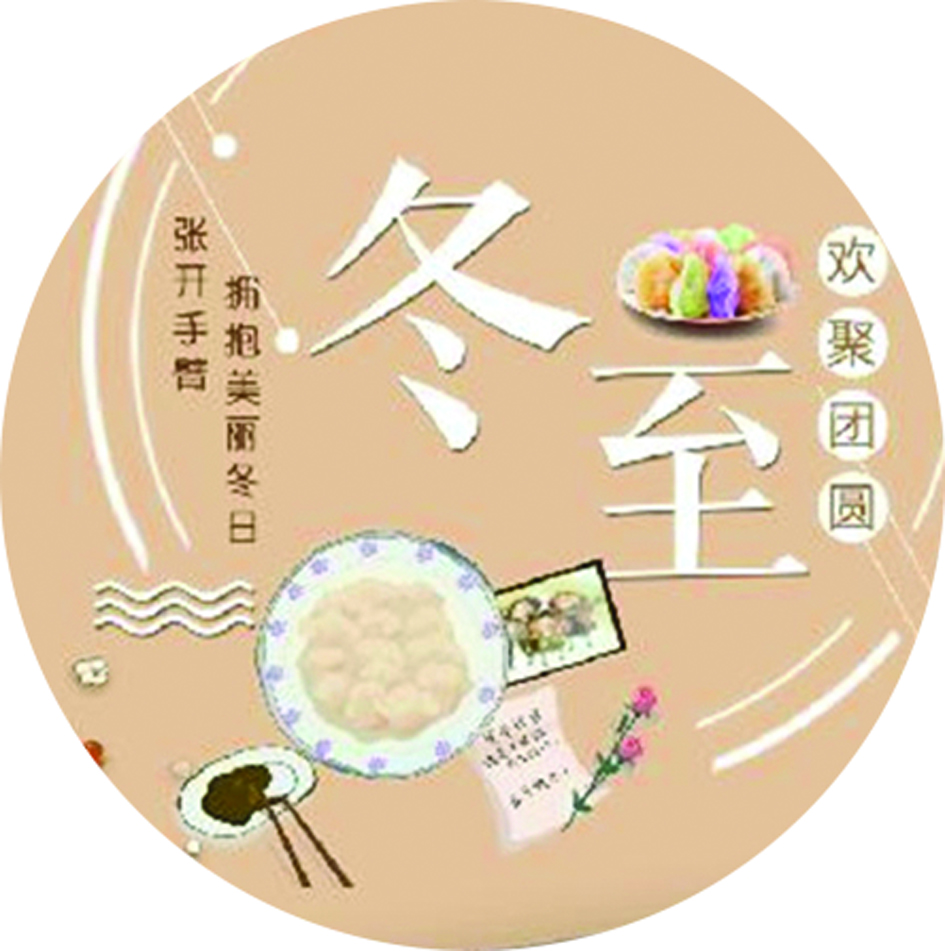冬至这两字,无论是看是读,都带着一点儿冷意的讯息:冬天来了。家中老人常念叨:数九寒天,过了冬至这一“数九”,就正式入冬了。
我一向奇怪,冬日的到来怎能这样快,分得这样清晰呢?它该是随着一场场雨和雪,一帧帧透明玻璃上多变的花样,一件件添上身的衣物,渐渐走到近前。现在想来古有古的道理。冬日稻麦已稔,新秧未插,正是悠悠闲闲享受成果的好时候,于是人们就寻个日子提醒彼此:该预备过年了。
你看我们多有意思,春天忙于劳作、爱情、繁衍,新鲜又充满希望,然而难免忙累,没时间欢庆祈祷,所以新的一岁不从别的,从冬天始,团聚寒暄、饮食贴膘,热闹非常。
冬至作为小年,可以算是新年的一次小小演习,曾经也热闹过一阵子。但到我们这辈,记忆里就没有太浓烈的声色,甚至浓缩为极小的一点。
比如说,一碗糊羹。
糊羹,照家乡话也读作“福羹”,确是黏糊糊浓稠的一大碗。江西地界按历正月初七吃糊羹,我家有些奇特,大概也不是根正苗红的老南昌后裔,规矩只学一半——糊羹放在冬至吃。
冬至那天,家里两个老人起个大早,“乒乒乓乓”在厨灶边忙活开,把胡萝卜、冬笋、香菇和腐竹洗净切丁,再照着法子伺候晒好的腊肉,切完昨夜新冻的鸭血和化开的鸭肚鸭颈子,按次序下锅,煸出香气。一旁早熬着一锅鸡汤,鸡是骟过的老鸡,煮出来汤汁清透光亮,上面一层浮油黄得可爱。这时把汤缓缓顺着锅沿倒入,各色的丁被汤汁激起,自如地旋转,像赣江水里浮沉的多彩的舟船。煮不多一会儿,就得上酱,老抽倒进去染上深色,具体还有哪些调味我现今记不真切,但一定有醋、香油和胡椒,若不然断不可能调出那样诱人的香气和风味。
糊羹糊羹,糊是第一要义。于是汤里头最后要添薯粉勾芡,一锅汤汁收个七八,留下极浓的羹。满一大锅初成,揭开盖来,温暖热乎的香气争先恐后地外奔,一会儿便占领了整个屋子。
老人家还未来得及喊早,年轻人和小孩子嗅着味儿便醒了。简单收拾一番就钉在桌前,几双眼睛巴望着那一口锅。等啊等,等了很久也不见端上来,性急的小跑两步到厨房,拿起烹调的大勺舀着往嘴里送,烫得舌头直往外抻。老一辈又欣慰又好笑,嗔怪一句:“去!看你急的——外面等着。”手推令行,身形一换,立时拦住了渴望的视线。
好呗,等着!等,等到他们慢条斯理把糊羹盛到砂钵里,晃晃悠悠端出小间,不急不缓垫好木板,再放到眼前。终于不用等了,赶忙拿把调羹破开碗沿一圈的油花,去舀洁白的老豆腐。汤匙缓缓没在羹里,往上抬,应付吹两口气就往嘴里送。小块蔬菜和汤在口中打了两转,豆腐缠绵地化在舌尖,同滑腻得几乎咬不着的菇子一起流向咽喉,那一股热腾腾的气顺着口腔、食道,一直暖到胃里。待到一碗糊羹下肚,又涨又暖,整个人熨帖极了,我才满足地喟叹一声,忽有所觉:
哦,冬至了。
许是贪嘴,我对节日的印象总和吃食脱不了干系。清明三月,草叶鲜肥,宜食艾草团;端午食粽,甜口的碱水蘸糖,喜荤的蛋黄夹肉,肉要精肥相杂,事先烹煮过,煮粽也不能用白水,各种汤料有个配比,煮出来的肉粽才口味黏糯,色泽深黄,一咬下去满嘴喷香;中秋吃月饼,广式油厚个大,苏式精致小巧,皮有油皮、冰皮、沙皮,馅从前是豆沙、莲蓉、五仁、椰蓉、凤梨、牛肉,现在多了水果、榴莲、海鲜、面筋等无数奇异事物,都高糖高热;重阳喝自家菊花酿、食栗子糕,菊花酒甜,入口甘美,后劲也大,栗子糕看个人喜好,重油的松软的香甜的都可;元宵当然来一碗汤圆,要芝麻花生馅的,水果不地道……原始时期祖先对食物的渴望烙在我的根骨里,节庆大喜,非要尝到那一口美味,才算过了个节。
冬至不能没有糊羹,正如南方长大的人正餐里不能少一碗米饭。吃菜、吞一碗面、包子馒头都能顶饱,但总觉着缺什么。冬至不食糊羹也能过,但不让杂混的食材们重逢腹中烫他一烫,肠胃也要委屈得泛酸水。
生平头一回到北国生活,不是没试过在此地找寻故乡的况味,也真在餐厅发现过瓦罐汤的招牌,然而终究是畏惧,畏惧异地相遇的已不是记忆中的风味,既不愿将就又缺乏胆量,长存念想却一次也未光顾……只能饿着。
这一饿,便由胃里直饿到心尖上。对故乡人、物、泥土和河流的思念,蔓草一般无可遏制地爬满心墙。张翰见秋风起,念及故里莼菜鲈鱼的鲜美辞官不做便回去了,我却不行。我得耐受着一声声“胡不归”,遥远无望地怀恋赣鄱水煮的一碗糊羹。
冬至已至,宜支锅生火、下杂料七八,煲汤作羹,待游子归矣。